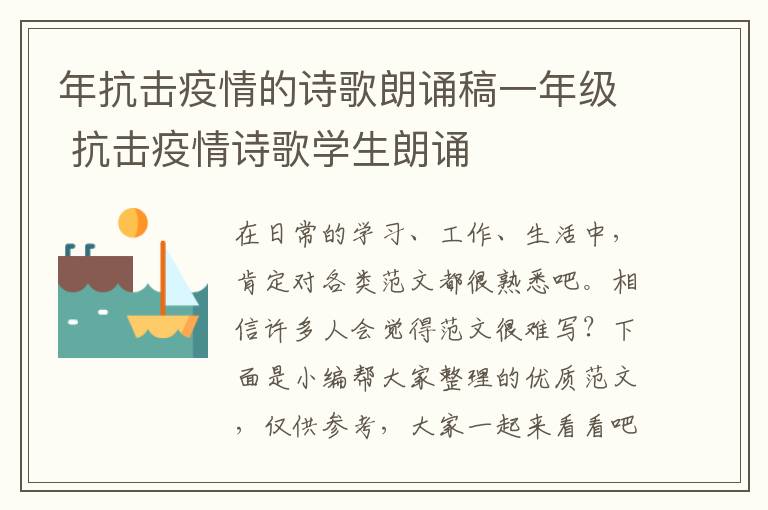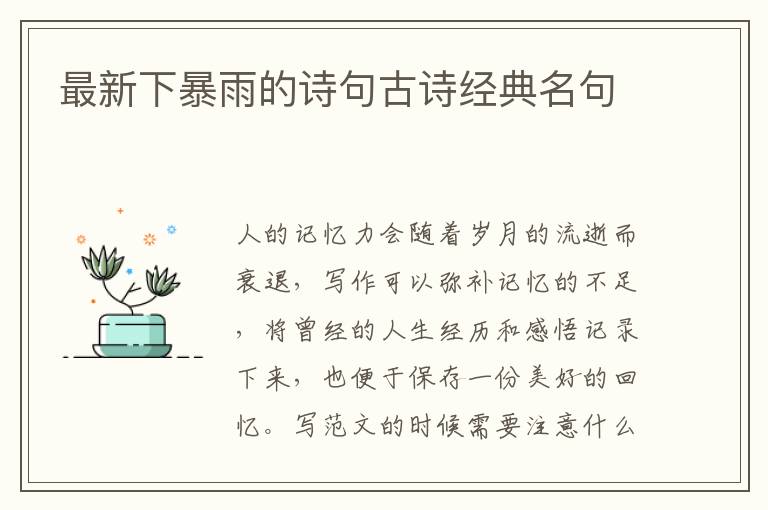西方文學(xué)·貝婁

西方文學(xué)·貝婁
美國(guó)小說(shuō)家,父母是俄國(guó)猶太移民,出生于加拿大魁北克的拉辛,從小就對(duì)暴力和性司空見慣,并在那兒學(xué)會(huì)了希伯來(lái)語(yǔ)、意第緒語(yǔ)、法語(yǔ)和英語(yǔ)。9歲時(shí)移居美國(guó)芝加哥。他是在大蕭條時(shí)期成熟的,因此,他的作品比較注重社會(huì)現(xiàn)實(shí)和文化背景; 貝婁不是自傳性作家,但永遠(yuǎn)寫他所熟悉的。《懸晃的人》(1944) 受陀斯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手記》的影響,聲稱是一個(gè)芝加哥人約瑟夫的日記,他總覺(jué)自己“懸而未決”,總在公民與軍人、理智與意欲、理論與經(jīng)驗(yàn)、溫順和暴躁之間“懸晃”。用貝婁評(píng)論赫索格 (貝婁小說(shuō)《赫索格》的主人公) 的話來(lái)說(shuō),“他開始認(rèn)識(shí)到,他以為那種理智的‘特權(quán)’實(shí)質(zhì)上是另一種枷鎖”,最后他催促軍方讓他應(yīng)征入伍。作品精巧,但態(tài)度晦澀,沒(méi)有情節(jié)。《受害者》 (1947) 也受陀氏《永恒的丈夫》的啟發(fā)而作,作品主題類似《懸晃的人》,講一個(gè)猶太人阿沙·列文塔爾受一個(gè)非猶太人阿爾比的威脅,要他為他找工作、提供食宿,列文塔爾于是感到了自己的不安全和犯罪感。很難說(shuō)阿爾比不是列文塔爾潛意識(shí)的產(chǎn)物。這部小說(shuō)的情節(jié)比《懸晃的人》有進(jìn)步,但結(jié)尾仍不能令人滿意。《奧奇·馬切歷險(xiǎn)記》 (1953) 講的是一個(gè)猶太青年馬切離家遠(yuǎn)游,通過(guò)各種生活經(jīng)歷學(xué)會(huì)了許多東西,最后在美國(guó)與一女演員結(jié)婚。他認(rèn)識(shí)到,“每個(gè)人的選擇都有其苦惱”,但人還是不愿過(guò)一種失望的生活,他要保持那種樂(lè)觀幽默和好奇。這部小說(shuō)首次拋棄了陀氏的影響,并采取了流浪漢小說(shuō)的形式,一方面小說(shuō)表現(xiàn)的內(nèi)容擴(kuò)大,一方面深入的心理分析加深了。1956年發(fā)表《抓住這一天》,1959年發(fā)表 《雨王漢德森》。吉恩·漢德森是美國(guó)的百萬(wàn)富翁,為了滿足內(nèi)心“我要、我要”的呼喊,他離開美國(guó)去非洲尋找智慧。來(lái)到瓦里里部落后,他幫他們祈雨成功而封為雨王,后被封為酋長(zhǎng)。根據(jù)瓦里里的傳統(tǒng),酋長(zhǎng)年老后一般被殺,其靈魂變成幼獅,要由繼任的酋長(zhǎng)捉住。漢德森于是帶著幼獅逃出了非洲。漢德森內(nèi)心的呼喊消失了。他也開始理解了自己。漢德林實(shí)質(zhì)上也是一位“懸晃的人”。此書象征之多及自然神秘主義色彩有似于海明威。《赫索格》發(fā)表于1964年,《賽姆勒先生的行星》 (1970) 講的是一個(gè)74歲的波蘭猶太人在紐約的故事。他在講演英國(guó)30年代戲劇情況時(shí)被人轟下臺(tái)后,街上的景象、車上的小偷及醫(yī)院里的死亡又使他暇想不已。賽姆勒是20世紀(jì)人類集體意識(shí)的代表,也是人類的代表,他在世界的混亂面前無(wú)能為力,而生理欲望又到了最低點(diǎn)。但他想飛離地球時(shí),他身上卻有某種本質(zhì)性的東西束縛著他,這是人類真正的價(jià)值所在; 叔本華式的悲觀主義和猶太教的樂(lè)觀主義充斥其間。最后,賽姆勒發(fā)育未全的心靈戰(zhàn)勝了理智。本書反映了一個(gè)自由派人道主義者對(duì)頹廢派的厭惡。《洪堡的禮物》發(fā)表于1975年。
索爾·貝婁是美國(guó)小說(shuō)界的紅星。曾獲1948至49年、55年到56年兩度“古根海姆獎(jiǎng)學(xué)金”,三度獲“國(guó)家圖書獎(jiǎng)” (分別為 《奧奇·馬切歷險(xiǎn)記》、《赫索格》、《賽姆勒先生的行星》),1976年獲諾貝爾獎(jiǎng)。嘉獎(jiǎng)詞中說(shuō),“在貝婁的著作中結(jié)合了對(duì)當(dāng)代文學(xué)中人性的理解和精細(xì)的分析”,“在我們這個(gè)搖搖欲墜的世界中,他小說(shuō)中的人物總是試圖找到其立足點(diǎn),這人總不放棄其信仰,他堅(jiān)信人類生活的價(jià)值在于其品德,而不在于成功與否。”諾貝爾獎(jiǎng)沒(méi)提到他小說(shuō)黑暗的一面,而這黑暗面正是其高超處。
貝婁作品的主題主要是講人生的多樣性及腐化,還有一個(gè)主題就是超脫物質(zhì)世界,我們這個(gè)世界其終極的問(wèn)題還是形而上且宗教的,,如一個(gè)社會(huì)造就了一顆心卻無(wú)法哺育它、一個(gè)世界要求人們扭曲自己才能在其勢(shì)力中生存、一個(gè)主人公竭盡全力以醫(yī)治一種無(wú)以名狀的病痛——這是典型的貝婁式主題。還有一個(gè)主題是猶太式的,小說(shuō)中的滑稽成份、理性主義、道德至上和異化感、對(duì)家庭的重視、認(rèn)為這個(gè)世界不真實(shí)、違背了上帝的初衷、對(duì)過(guò)去的懷戀、東歐移民主人公等,都表明他在內(nèi)心深處是一個(gè)真正的猶太人。
藝術(shù)上,貝婁一方面繼承了現(xiàn)實(shí)主義的表現(xiàn)手法,重于社會(huì)與歷史的真實(shí)反映; 另一方面則汲取了現(xiàn)代主義著重心理世界的新手法,大量運(yùn)用了意識(shí)流技巧,把人物的內(nèi)心獨(dú)白、思緒感受、所寫的書信、回憶與欲望及現(xiàn)實(shí)圖景夾雜一起,跳蕩變幻。貝婁是語(yǔ)言大師,其語(yǔ)言具有喜劇風(fēng)格,幽默而滑稽和典雅精致混合一體,璣珠之詞與妙語(yǔ)警句相映成輝,激情與感傷的情調(diào)隨文而下。他的作品情節(jié)性差,而人物感受又極豐富,在其中找不到一個(gè)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