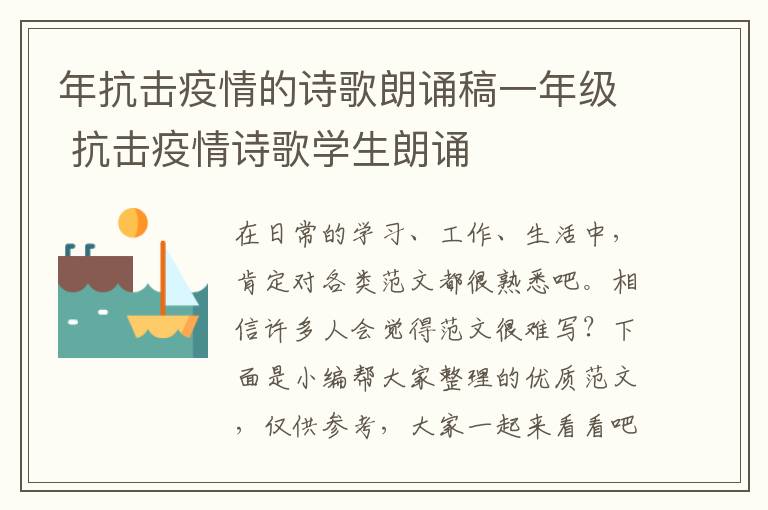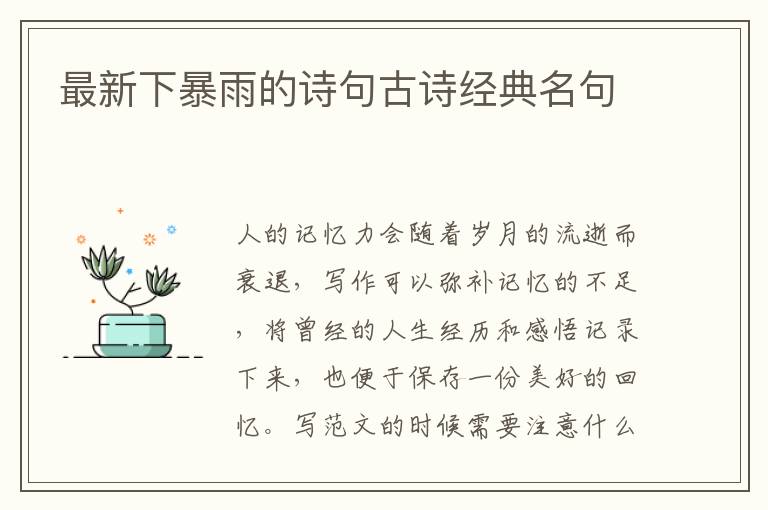郭沫若:中國(guó)詩(shī)文化的自由形態(tài)與自覺形態(tài)

郭沫若:中國(guó)詩(shī)文化的自由形態(tài)與自覺形態(tài)
我們要把固有的創(chuàng)造精神恢復(fù),我們要研究古代的精華,吸收古人的遺產(chǎn),以期繼往而開來。
——郭沫若:《文藝論集·一個(gè)宣言》
從出現(xiàn)在五四詩(shī)壇的那一天起,郭沫若就與眾不同地公開宣布“要研究古代的精華,吸收古人的遺產(chǎn)”,將“開來”與“繼往”緊密地結(jié)合起來。他歷數(shù)泰戈?duì)枴⒒萏芈⒏璧碌鹊韧鈦淼挠绊懀舱諛右辉僦貜?fù)著屈原、陶淵明、王維、李白、孟浩然等中國(guó)古典詩(shī)人的啟蒙意義,直到解放以后,詩(shī)人還堅(jiān)持說:“新詩(shī)在受了外來的影響的同時(shí),并沒有因此而拋棄了中國(guó)詩(shī)歌的傳統(tǒng)。”因此,中國(guó)傳統(tǒng)文化作為“原型”的意義在郭沫若那里特別地引人注目,它顯然已經(jīng)從無意識(shí)被提煉為意識(shí),從不自覺上升為自覺了。
1.詩(shī)的自由與自覺
從郭沫若的自述來看,投合他的情感,給他深遠(yuǎn)影響的中國(guó)古典詩(shī)人實(shí)在不少,不過,認(rèn)真清理起來,又似乎分為兩大類:一是以屈原為代表的先秦詩(shī)歌,二是以陶淵明、王維等人為代表的晉唐詩(shī)歌。他說:“屈原是我最喜歡的一位作家,小時(shí)候就愛讀他的作品。”還在舊體詩(shī)中滿懷感情地吟嘆:“屈子是吾師,惜哉憔悴死,”在多次的童年記述中,詩(shī)人又談到了晉唐詩(shī)歌給他“莫大的興會(huì)”,其中,以陶淵明、王維為代表。比如在1936年關(guān)于《女神》、《星空》的創(chuàng)作談里,郭沫若說:“至于舊詩(shī),我喜歡陶淵明、王維,他倆的詩(shī)有深度的透明,其感觸如玉。李白寫的詩(shī),可以說只有平面的透明,而陶王卻有立體的透明。”以屈原為典型的詩(shī)歌形態(tài)和以陶淵明、王維為典型的詩(shī)歌形態(tài)就是郭沫若詩(shī)歌藝術(shù)的原型。
值得注意的是,這兩大原型形態(tài)實(shí)際上代表著中國(guó)古典詩(shī)歌史上的兩個(gè)重要的發(fā)展階段:原始階段與成熟階段,或者說是自由的階段與,自覺的階段。
屈原及其創(chuàng)作的楚辭是中國(guó)古典詩(shī)歌的自由形態(tài),其基本特征是:(1)自我與個(gè)性得到了較多的尊重。如《離騷》滿篇流溢著詩(shī)人那恢宏壯麗的個(gè)人抱負(fù),那“鷙鳥不群”的錚錚傲骨。開篇8句(今人斷句),出現(xiàn)“我”(朕、吾、余等)就達(dá)6處之多,這在后世是難以想象的。(2)人不僅在客觀世界中取得了相對(duì)的獨(dú)立性,還可以反過來調(diào)理、選擇客觀世界(自然與社會(huì))。《離騷》的痛苦包含著他在選擇生存環(huán)境時(shí)的兩難;而詩(shī)人也盡可以“乘騏驥以馳騁兮”(《離騷》),“登九天兮撫彗星”(《少司令》),逐龍喚鳳,驅(qū)日趕月,擁有無上的權(quán)威。(3)詩(shī)歌以意象的玄奇絢麗取勝,“弘博麗雅”(班固語(yǔ)),“奧雅宏深”(汪瑗語(yǔ))。(4)全詩(shī)富于曲折、變化,顯示出一種開闔倏忽的動(dòng)態(tài)美。
陶淵明、王維所代表的晉唐詩(shī)歌屬于中國(guó)古典詩(shī)歌的自覺形態(tài)。中國(guó)詩(shī)歌在這一時(shí)期由自由走向成熟,恰恰是中國(guó)傳統(tǒng)文化“大一統(tǒng)”、“超穩(wěn)定”的產(chǎn)物。“大一統(tǒng)”、“超穩(wěn)定”為中國(guó)文人提供了較先秦時(shí)代相對(duì)坦蕩的出路,但卻剝奪了那縱橫馳騁的自由選擇,中國(guó)文人被確定為一個(gè)嚴(yán)密系統(tǒng)中的有限的、微弱的個(gè)體,從屬于自我的本性就這樣日漸消融,或散失在了社會(huì)當(dāng)中,或淡化在了自然當(dāng)中,儒釋道的成熟和它們之間的融洽共同影響著中國(guó)詩(shī)歌自覺形態(tài)的基本特征:(1)自我的消解、個(gè)性的淡化。(2)人接受著客觀世界的調(diào)理,追求天人合一。(3)詩(shī)歌追求圓融渾成的意境,“隱秀”是其新的美學(xué)取向。(4)詩(shī)歌的典型氣質(zhì)是恬淡無為,顯示出一種寧?kù)o致遠(yuǎn)的靜態(tài)美。當(dāng)然,不是所有的晉唐詩(shī)歌都是這樣的沖淡平和,以境取勝,但是,陶、王的詩(shī)歌傾向卻代表了中國(guó)詩(shī)文化在自覺時(shí)期最獨(dú)特、影響最深遠(yuǎn)的抉擇,尤其符合郭沫若當(dāng)時(shí)的理解。
不言而喻,從思想到藝術(shù),自由的詩(shī)和自覺的詩(shī)所給予郭沫若的原型啟示都是各不相同的。那么,郭沫若又是如何看待這樣的差別呢?屈原所代表的“先秦自由”向來為詩(shī)人所推崇,而陶、王的“晉唐自覺”也同樣契合著他的需要。詩(shī)人曾經(jīng)比較屈原與陶淵明這一對(duì)“極端對(duì)立的典型”,說:“我自己對(duì)于這兩位詩(shī)人究竟偏于哪一位呢,也實(shí)在難說。照近來自己的述作上說來,自然是關(guān)于屈原的多。”“然而……凡是對(duì)于老、莊思想多少受過些感染的人,我相信對(duì)于陶淵明與其詩(shī),都是會(huì)起愛好的念頭的。”“那種沖淡的詩(shī),實(shí)在是詩(shī)的一種主要的風(fēng)格。”在另外一個(gè)場(chǎng)合,他又表示:“我自己本來是喜歡沖淡的人,譬如陶詩(shī)頗合我的口味,而在唐詩(shī)中我喜歡王維的絕詩(shī),這些都應(yīng)該是屬于沖淡的一類。”可見,郭沫若對(duì)這樣的差別不以為然,他在五四時(shí)代的文化寬容精神也包括了對(duì)差別本身的寬容。
自由與自覺作為原型的意義就這樣被確定了下來,并在詩(shī)人主體意識(shí)的深處發(fā)揮著決定性的作用。
2.自由與自覺的循環(huán):郭沫若的詩(shī)歌之路
中國(guó)古典詩(shī)文化的自由形態(tài)與自覺形態(tài)是郭沫若用以迎納、解釋、接受西方詩(shī)潮的基礎(chǔ),正如莊子、王陽(yáng)明是他認(rèn)同西方“泛神論”的基礎(chǔ)一樣。中國(guó)古典詩(shī)文化的原型形態(tài)為時(shí)代精神所激活,在西方詩(shī)潮的沖擊下生成了它的現(xiàn)代模式,這些現(xiàn)代模式往往包含著較多的現(xiàn)代性和西方化傾向,但追根究底,仍然扭結(jié)在中國(guó)傳統(tǒng)文化精神當(dāng)中。是中國(guó)古典詩(shī)文化決定了郭沫若向西方世界選取什么和怎樣選取。
“創(chuàng)造十年”結(jié)束后,郭沫若有過一段著名的自述:
我的短短的做詩(shī)的經(jīng)過,本有三四段的變化。第一段是太戈?duì)柺剑谝欢螘r(shí)期在“五四”以前,做的詩(shī)是崇尚清淡、簡(jiǎn)短,所留下的成績(jī)極少。第二段是惠特曼式,這一段時(shí)期正在“五四”的高潮中,做的詩(shī)是崇尚豪放、粗暴,要算是我最可紀(jì)念的一段時(shí)期。第三段便是歌德式了,不知怎的把第二期的熱情失掉了,而成為韻文的游戲者。
盡管他的自我闡釋借用了西方詩(shī)人的形象,幾個(gè)階段的劃分也顯得比較復(fù)雜,但是,一旦我們結(jié)合詩(shī)人的其他一些重要的自述加以分析,特別是深入到他的詩(shī)歌藝術(shù)世界之中,問題就比較清楚,比較單純了。導(dǎo)致郭沫若詩(shī)歌如此三番五次的轉(zhuǎn)折變化,其重要的原因是可以在中國(guó)古典詩(shī)歌的原型那里尋找的,是自由形態(tài)與自覺形態(tài)的互相消長(zhǎng)推動(dòng)著詩(shī)人內(nèi)在的精神需要發(fā)生著波動(dòng)性的變化,而變化也不是漫無邊際、難以捉摸的,或者是自由精神的增加,或者是自覺意識(shí)的上升,是自由與自覺的循環(huán)前進(jìn)。
在《我的作詩(shī)經(jīng)過》一文中,郭沫若將泰戈?duì)柺降臎_淡與陶、王等人的沖淡聯(lián)系在一起,這說明,在他剛剛踏上詩(shī)歌創(chuàng)作道路之時(shí),中國(guó)古典詩(shī)歌的自覺形態(tài)起著主要作用,這或許是每一個(gè)中國(guó)現(xiàn)代詩(shī)人都難以避免的詩(shī)歌啟蒙時(shí)期吧,晉唐詩(shī)歌畢竟是中國(guó)現(xiàn)代詩(shī)人蒙學(xué)教育的最主要的內(nèi)容。在郭沫若特有的“創(chuàng)造性誤解”中,印度現(xiàn)代詩(shī)人泰戈?duì)杽?chuàng)作的“沖淡”喚起了他“似曾相識(shí)”的親近感,鼓勵(lì)著他進(jìn)行“中西結(jié)合”的選擇。
五四時(shí)代,隨著個(gè)性解放呼聲的高漲,文學(xué)革命的蓬勃展開,惠特曼詩(shī)歌的傳播,郭沫若那固有的自由基因又生長(zhǎng)了起來。此時(shí)此刻,他所理解的“精赤裸裸的人性”、“同環(huán)境搏斗的”“動(dòng)態(tài)的文化精神”以及“自我擴(kuò)充”、“藐視一切權(quán)威的反抗精神”都是先秦文化的固有表現(xiàn),而屈原及其楚辭便是先秦文化的詩(shī)歌表述。所以說,郭沫若眼中的屈原多少都有點(diǎn)自我投射的影子:
屈原所創(chuàng)造出來的騷體和之乎也者的文言文,就是春秋戰(zhàn)國(guó)時(shí)代的白話文,在二千年前的那個(gè)時(shí)代,也是有過一次五四運(yùn)動(dòng)的,屈原是五四運(yùn)動(dòng)的健將。
《女神》就是郭沫若創(chuàng)造出來的自由形態(tài)的騷體。在《女神》之中,郭沫若塑造了一個(gè)個(gè)打倒偶像、崇尚創(chuàng)造、意志自由的“我”,他假借《湘累》里屈原的口說:“我效法造化底精神,我自由創(chuàng)造,自由地表現(xiàn)我自己。”《女神》極力標(biāo)舉自我的地位,而客觀世界則是“我”創(chuàng)造、吞噬和鞭策的對(duì)象,也是“我”的精神的外化。《湘累》有云:“我創(chuàng)造尊嚴(yán)的山岳、宏偉的海洋,我創(chuàng)造日月星辰,我馳騁風(fēng)云雷雨,我萃之雖僅限于我一身,放之貝可泛濫乎宇宙。”“我有血總要流,有火總要噴,不論在任何方面,我都想馳騁!”《天狗》“我把月來吞了,/我把日來吞了,/我把一切的星球來吞了,/我把全宇宙來吞了。”《日出》中的太陽(yáng)成了奔騰生命的象征:“哦哦,摩托車前的明燈!/你二十世紀(jì)底亞坡羅!/你也改乘了摩托車嗎?”與屈騷相類似,《女神》色彩絢麗,意象繁密,充滿了波瀾起伏的動(dòng)態(tài)美,——包括奔突不息的形體運(yùn)動(dòng)和急劇變遷的思想運(yùn)動(dòng)。如《立在地球邊上放號(hào)》:“無限的太平洋提起他全身的力量來要把地球推倒。/啊啊!我眼前來了的滾滾的洪濤喲!/啊啊,不斷的毀壞,不斷的創(chuàng)造,不斷的努力喲!”這是形體的運(yùn)動(dòng);又如《鳳凰涅槃》:“宇宙呀,宇宙,/你為什么存在?/你自從哪兒來,/你坐在哪兒在?/你是個(gè)有限大的空球?/你是個(gè)無限大的整塊?/你若是有限大的空球……”這是思想的運(yùn)動(dòng)。
1921、1922年兩年中,郭沫若多次回國(guó),耳聞目睹的事實(shí)徹底摧毀了他復(fù)興先秦文化精神的幻想,“哀哭我們墮落了的子孫,/哀哭我們墮落了的文化,/哀哭我們滔滔的青年”(《星空》)。為了舒散這些“深沉的苦悶”,詩(shī)人轉(zhuǎn)向了他所自稱的“歌德式”的創(chuàng)作。不過,所謂“熱情失掉了,而成為韻文的游戲者”卻并不是睿智而執(zhí)著的歌德的本來面目,就其實(shí),倒更像是中國(guó)詩(shī)歌自覺原型的第二次復(fù)活。如《雨后》:
雨后的宇宙,
好像淚洗過的良心,
寂然幽靜。
海上泛著銀波,
天空還暈著煙云,
松原的青森!
平平的岸上,
漁舟一列地驕陳,
無人蹤印。
有兩三燈光,
在遠(yuǎn)遠(yuǎn)的島上閃明——
初出的明星?
這很容易就讓人想起了王維的《山居秋暝》:“空山新雨后,天氣晚來秋。明月松間照,清泉石上流。竹喧歸浣女,蓮動(dòng)下漁舟。隨意春芳歇,王孫自可留。”
自由是中國(guó)詩(shī)人在社會(huì)動(dòng)蕩期個(gè)性展示的需要,自覺則是在社會(huì)穩(wěn)定期聊以自慰的產(chǎn)物。有趣的是,這一歷史規(guī)律也在郭沫若身上反映了出來。留學(xué)海外的詩(shī)人,熱情勃發(fā),思維活躍,他很容易地舉起了自由的旗幟;而一當(dāng)他不得不面對(duì)中國(guó)社會(huì)穩(wěn)固沉寂的現(xiàn)實(shí)時(shí),自由就成了毫無意義的空想,于是,自覺的原型便悄悄地襲上心來。
但歷史又給郭沫若提供了一次自由的機(jī)會(huì)。1923年以后,隨著社會(huì)革命的發(fā)展,特別是郭沫若對(duì)馬克思主義思想的接觸、認(rèn)識(shí),他那抑制著、沉睡著的斗爭(zhēng)欲、反抗欲獲得了較先前更為強(qiáng)大的支撐,于是《前茅》、《恢復(fù)》問世了。“前茅”是革命的、反抗的“前茅”,而“恢復(fù)”則象征著詩(shī)人從“深沉的苦悶”中“復(fù)活”了堅(jiān)強(qiáng)的意志,“要以徹底的態(tài)度撒尿”,“要以意志的力量拉屎”(《恢復(fù)》)。過去一般認(rèn)為,《前茅》、《恢復(fù)》時(shí)期的郭沫若是對(duì)“從前深帶個(gè)人主義色彩的想念”之反動(dòng),而詩(shī)人自己也明確地表示:“我從前是尊重個(gè)性、景仰自由的人,但是最近一兩年間與水平線下的悲慘社會(huì)略略有所接觸,覺得在大多數(shù)人完全不自主地失掉了自由,失掉了個(gè)性的時(shí)代,有少數(shù)的人要來主張個(gè)性,主張自由,未免出于僭妄。”其實(shí),只要認(rèn)真分析一下這一時(shí)期的詩(shī)歌,我們就不難透過那些“粗暴的喊叫”,見到詩(shī)人那怦怦跳動(dòng)著的渴望自由、渴望自我展示的心,——當(dāng)他以所有受壓迫者的代言人自居,大聲疾呼,狂放不羈時(shí),《女神》式的品格、《女神》式的詩(shī)學(xué)追求便清晰地呈現(xiàn)了出來:
革命家的榜樣就在這粗俗的話中,
我要保持態(tài)度的徹底,意志的通紅,
我的頭顱就算被人鋸下又有甚么?
世間上決沒有兩面可套弦的彎弓。
《恢復(fù)》
那么,繼中國(guó)古典詩(shī)歌自由原型的第二次復(fù)活之后,自覺原型是不是也再一次地被激活了呢,從表面上看,包括抗戰(zhàn)時(shí)期的《蜩螗集》、《戰(zhàn)聲集》以及解放以后的《新華頌》、《潮集》、《駱駝集》、《東風(fēng)集》等都洋溢著革命的激情,似與陶、王的“沖淡恬靜”相去甚遠(yuǎn),但是,考慮到詩(shī)久在這一時(shí)期,特別是解放以后的特殊地位,我們則可以肯定地認(rèn)為,郭沫若已經(jīng)沒有可能再狂放不羈、“粗暴的喊叫”了,從理論上講,他無疑將進(jìn)入到自覺的形態(tài)。于是,我們不得不特別注意這樣的事實(shí):在這一時(shí)期,郭沫若詩(shī)歌創(chuàng)作最重要的現(xiàn)象便是大量的舊體詩(shī)詞的出現(xiàn),而我們知道,中國(guó)古典詩(shī)歌正是在晉唐時(shí)代確立了自己的典型形式,自覺原型的第三次復(fù)活似乎首先就表現(xiàn)在詩(shī)歌藝術(shù)的形式之中;此外,我們還注意到,在郭沫若的舊體詩(shī)詞中,亦不時(shí)流出這樣的句子:
山頂日當(dāng)午,流溪一望中。時(shí)和風(fēng)習(xí)習(xí),氣暖水溶溶。鳥道盤松嶺,膠輪輾玉虹。太空無片滓,四壁聳青峰。(《遠(yuǎn)眺》)
北海曾來此,巖前有舊題。洞天天外秀,福地地中奇。膏炬延游艇,葵羹解渴絲。留連不忍去,無怪日遲遲。(《游端州七星巖·游碧霞洞》)
芙蓉花正好,秋水滿湖紅。雙艇觀魚躍,三杯待蟹烹。鶯歸余柳浪,雁過醒松風(fēng)。樵舍句山在,伊人不可逢。(《訪句山樵舍》)
居高官,忙政務(wù),自然已不再是“沖淡”的時(shí)候了,但偶得閑暇,忘情于山水之間,那意識(shí)深處的傳統(tǒng)文化原型還會(huì)浮現(xiàn)出來。
總而言之,在郭沫若的詩(shī)歌藝術(shù)生涯中,中國(guó)詩(shī)文化的自由形態(tài)與、自覺形態(tài)始終生生不息,循環(huán)往復(fù),發(fā)揮著至關(guān)緊要的作用。《星空》題序中郭沫若曾引用康德的名言說:“有兩樣?xùn)|西,我思索的回?cái)?shù)愈多,時(shí)間愈久,他們充溢我以愈見刻刻常新,刻刻常增的驚異與嚴(yán)肅之感,那便是我頭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律。”結(jié)合郭沫若的創(chuàng)作實(shí)踐來看,他顯然是不無中國(guó)特色地把“星空”詮釋為身外的客觀世界,而把自我的自由意志、生存原則詮釋為“心中的道德律”,前者誘惑詩(shī)人進(jìn)入自覺,而后者則激發(fā)著人的自由。于是,中國(guó)詩(shī)歌原型的自由與自覺就的確是“刻刻常新”,“刻刻常增”“驚異與嚴(yán)肅之感”的。
3.自由與自覺的消長(zhǎng):郭沫若精神結(jié)構(gòu)之一瞥
在我們運(yùn)用自由與自覺的原型意義,對(duì)郭沫若詩(shī)歌創(chuàng)作道路作了一個(gè)簡(jiǎn)略回顧之后,我認(rèn)為有兩點(diǎn)必須特別指出:
(1)所謂自由與自覺的循環(huán)生長(zhǎng)只是我們對(duì)問題的比較粗糙的梗概性說明,實(shí)際上,除了這樣有規(guī)律的演變之外,這兩大原型形態(tài)的關(guān)系還要復(fù)雜得多,比如,在同一創(chuàng)作時(shí)期,自由與自覺也可能同時(shí)顯示自己的力量,以至對(duì)郭沫若的詩(shī)歌創(chuàng)作造成一言難盡的影響。
(2)有趣的還在于,盡管郭沫若經(jīng)歷了這樣曲折的詩(shī)風(fēng)變化,盡管他也看到了自由原型與自覺原型給予自身的影響,但是顯而易見,詩(shī)人并沒有清醒地意識(shí)到這兩大詩(shī)歌形態(tài)在他詩(shī)歌藝術(shù)中的特殊地位——它們的循環(huán)生長(zhǎng)以及相互間的分歧、矛盾。
綜合這兩個(gè)方面,我們可以得出一個(gè)什么樣的結(jié)論呢?我認(rèn)為,這已經(jīng)清楚地表明,在郭沫若的精神結(jié)構(gòu)中,自由與自覺又隱隱地呈現(xiàn)為一種彼此消長(zhǎng)、相生相克的關(guān)系,生中有克,克中有生。
首先我們看生中有克。
自由與自覺共生于郭沫若詩(shī)歌發(fā)展的同一個(gè)時(shí)期,但是,由于它們?cè)谒枷胍饬x、藝術(shù)境界上的分歧、矛盾,郭沫若的詩(shī)歌因此而出現(xiàn)了若干詩(shī)學(xué)追求中的迷茫與瞀亂,這就是所謂的“克”。特別是當(dāng)這兩種原形都竭力在同一首詩(shī)中顯示自己的意義時(shí),其內(nèi)在的裂痕就不可避免地裸露了出來。總的說來,自由喚起詩(shī)人的自我意識(shí),要求對(duì)自我的“突現(xiàn)”,而自覺則極力消融自我意識(shí),要求對(duì)自我實(shí)行“忘卻”;自由讓主體的形象與思想在詩(shī)中縱橫,而自覺則一再陶醉在天人合一的境界之中。突現(xiàn)與忘卻、縱橫與陶醉作為兩種分離的詩(shī)歌藝術(shù)傾向不時(shí)雜糅在一起,構(gòu)成了郭沫若詩(shī)歌特有的駁雜特色。
如《鳳凰涅槃》,西方的“菲尼克司”(Phoenix)“集香木自焚”,顯然是自由意志的表現(xiàn),詩(shī)中也突現(xiàn)了它的意志和思想,讓它在咒天詛地中馳騁自己的感情,但是,當(dāng)它“從死灰中更生”時(shí),竟展示了這樣的自由景象:
一切的一,和諧。
一的一切,和諧。
和諧便是你,和諧便是我。
和諧便是他,和諧便是火。
火便是你。
火便是我。
火便是他。
火便是火。
……
不分你我他,不分自我與世界,所有的山川草木、飛禽走獸和人類都籠罩在一片和諧之中,這恰恰是中國(guó)詩(shī)文化自覺原型的精神。在中國(guó)文化中,如此突出“一”的哲學(xué)意義,也正是晉唐時(shí)代儒道釋日漸“三教合一”的特征,只有在這個(gè)時(shí)候,老子的“道生一”,“圣人抱一為天下式”(《老子》),孔子的“吾道一以貫之”(《論語(yǔ)·里仁》),佛學(xué)的“空”才被中國(guó)文人如此運(yùn)轉(zhuǎn)自如地把玩著。自覺最終掩蓋了自由。
又如《西湖紀(jì)游·雨中望湖》:
雨聲這么大了,
湖水卻染成一片粉紅。
四圍昏蒙的天
也都帶著醉容。
浴沐著的西子喲,
裸體的美喲!
我的身中……
這么不可言說的寒噤!
哦,來了幾位寫生的姑娘,
可是,unschoeh。
unschoeh意即不美麗,不漂亮。顯然,郭沫若本來處于“自失”狀態(tài),“忘卻”了自我,沉醉于西湖迷蒙的雨景當(dāng)中。但是,其心未“死”,意識(shí)還在隱隱地蠕動(dòng),所以當(dāng)異性——映入到他的眼簾,自我的欲望和思想就迸射了出來。自由完成了對(duì)自覺的排擠。
類似的例子還有《梅花樹下的醉歌》、《晚步》、《雪朝》等等。
不過,我們也沒有必要格外夸大“自由”與“自覺”的矛盾對(duì)立關(guān)系,因?yàn)椋鼈冸m有種種的分歧,但畢竟又同屬于中國(guó)古典詩(shī)文化范疇內(nèi)的兩種原型,有對(duì)立的一面,更有統(tǒng)一的一面;自覺形態(tài)與自由形態(tài)再不同,也還是它輾轉(zhuǎn)變遷的產(chǎn)物。以屈騷為代表的中國(guó)先秦詩(shī)歌再個(gè)性自由、自我突出,也終究不能與西方詩(shī)歌,尤其是19世紀(jì)的浪漫主義詩(shī)歌相提并論,先秦文化的自由和晉唐文化的自覺都有各自特殊的“中國(guó)特色”。
先秦文化的自由并沒有取得西方式的絕對(duì)的、本體性的意義,它是相對(duì)的,又與個(gè)人的一系列特定的修養(yǎng)相聯(lián)系。這些修養(yǎng)大體上包括了諸如宗法倫理、內(nèi)圣外王的道德化人格、先賢遺訓(xùn)以及雛形的“修齊治平”等等內(nèi)容,在屈騷中,這些內(nèi)涵是非常明顯的。事實(shí)上,這已經(jīng)就孕育了消解自我、天人合一的可能性(“天”有多重含義,可以是自然,也可以是天理、國(guó)家民族之大義等等),為自覺時(shí)期中國(guó)詩(shī)文化的本質(zhì)追求奠定了基礎(chǔ)。相應(yīng)地,晉唐文化的自覺又沒有完全取消先秦式的自由,談到個(gè)人的修養(yǎng),包括陶淵明這樣的詩(shī)人都無一例外地看重人倫道德,崇尚先賢風(fēng)范,晉唐詩(shī)人依然自由地表述著自我的思想情感,只不過,他們將更多的“自我之外”的精神因素(自然生命或者民族責(zé)任)內(nèi)化為個(gè)人的思想情感,是自覺中的自由。
自由原型和自覺原型在深層結(jié)構(gòu)上的這種一致性被郭沫若領(lǐng)悟和接受著,并由此形成了郭沫若詩(shī)學(xué)追求“多中見一”、“雜中有純”的特色,這也就是我們所謂的克中有生。克中有生是我們窺視郭沫若詩(shī)歌深層精神的一把鑰匙。
自《女神》以降,郭沫若的自由追求深受著屈騷精神的影響:自由不是純個(gè)體意義的,當(dāng)然更不是絕對(duì)的,它總是以民族的救亡圖存為指歸,“不愿久偷生,但愿轟烈死。愿將一己命,救彼蒼生起,”(《棠棣之花》)自我也并不是無所顧忌地追逐個(gè)人的利益和幸福,他常常以濟(jì)世者自居,又站在濟(jì)世者的道德立場(chǎng)上去觀察世界和他人,這樣,“匪徒”就成了獻(xiàn)身社會(huì)的仁人志士(《匪徒頌》),而勞動(dòng)人民也成了憐惜、同情的對(duì)象(《輟了課的第一點(diǎn)鐘里》、《地球,我的母親》、《雷峰塔下·其一》),郭沫若從來不開掘自我的內(nèi)在精神狀態(tài),從來不對(duì)人的精神自由作出更復(fù)雜更細(xì)致也更恢宏的認(rèn)識(shí),也較少表現(xiàn)自我與自由在現(xiàn)存世界面臨的種種苦況與艱難,而這些又都是真正的現(xiàn)代自由所必須解決的問題。郭沫若更習(xí)慣于在中國(guó)原型形態(tài)的定義上來呈現(xiàn)“自由”,來“呼應(yīng)”西方浪漫主義詩(shī)歌。這就帶來了一個(gè)結(jié)果,即當(dāng)詩(shī)人要如西方詩(shī)人似的竭力突出自我、揮灑自由時(shí),他便顯得有些中氣不足,內(nèi)在的空虛暴露了出來。《天狗》可能是郭沫若最狂放自由的作品,但是,在我看來,從吞噬宇宙到吞噬自我,“天狗”的精神恰恰是混亂的,迷茫的,缺乏真正的震撼人心的力度。有時(shí)候,詩(shī)人為了表現(xiàn)自身的創(chuàng)造力量,無休止地將中外文化的菁華羅列起來,堆積起來:“我喚起周代的雅伯,/我喚起楚國(guó)的騷豪,/我喚起唐世的詩(shī)宗,/我喚起元室的詞曹,/作《吠陀》的印度古詩(shī)人喲,/作《神曲》的但丁喲,/作《失樂園》的米爾頓喲,/作《浮士德》悲劇的歌德喲!”(《創(chuàng)造者》)但一個(gè)創(chuàng)造者究竟當(dāng)有什么樣的氣魄呢?我們所見有限。到了《前茅》、《恢復(fù)》時(shí)期,這種自由與抗?fàn)幍目斩葱跃透用黠@了。有時(shí)候,連詩(shī)人自己也深有體會(huì):“我是詩(shī),這便是我的宣言,/我的階級(jí)是屬于無產(chǎn);/不過我覺得還軟弱了一點(diǎn),/我應(yīng)該要經(jīng)過爆裂一番。/這怕是我才恢復(fù)不久,俄的氣魄總沒有以前雄厚。/我希望我總有一天,/我要如暴風(fēng)一樣怒吼。”(《詩(shī)的宣言》)
自我意識(shí)的收縮,自由精神的空疏,這決定了郭沫若對(duì)待客觀世界的態(tài)度。我們看到,盡管詩(shī)人面對(duì)高山大海時(shí)常升騰起對(duì)生命的贊頌,時(shí)常喚起一種激動(dòng)人心的崇高體驗(yàn),但是,他卻始終把自己放在了這么一個(gè)“被感染”、“被召喚”的位置,西方浪漫主義詩(shī)歌中人與自然相搏斗、相撞擊的景觀并沒有得到更多的表現(xiàn)。從這個(gè)邏輯出發(fā),當(dāng)詩(shī)人的自我和自由在實(shí)踐中被進(jìn)一步刪削、稀釋之后,客觀世界便理所當(dāng)然地顯出一些威嚴(yán)恐怖的氣象,給詩(shī)人以壓迫、以震懾:“啊,我怕見那黑沉沉的山影,/那好像童話中的巨人!/那是不可抵抗的……”(《燈臺(tái)》)詩(shī)人在客觀世界的風(fēng)暴中沉浮,久而久之,他終于疲倦了,衰弱了:“一路滔滔不盡的濁潮/把我沖蕩到海里來了。”“滔滔的濁浪/早已染透了我的深心。/我要幾時(shí)候/才能恢復(fù)得我的清明喲?”(《黃海中的哀歌》)
當(dāng)人在客觀世界面前感嘆自身力量的弱小,而又并沒有獲得更強(qiáng)勁更堅(jiān)韌的支持時(shí),天人合一的理想便誕生了。在對(duì)民族大義的鏗鏘激動(dòng)中,在澄淡精致的大自然中,我們那疲弱的心靈才找到了更踏實(shí)更妥帖的依托。于是,中國(guó)詩(shī)歌便轉(zhuǎn)向了自覺形態(tài)。自由到自覺就這樣實(shí)現(xiàn)了它的內(nèi)在的過渡,自由與自覺的循環(huán)便是以此為基點(diǎn)、軸心的。
在《星空·孤竹君之二子》的“幕前序話”里,郭沫若闡發(fā)了他關(guān)于傳統(tǒng)文化的基本觀念:“天地間沒有絕對(duì)的新,也沒有絕對(duì)的舊。一切新舊今古等等文字,只是相對(duì)的,假定的,不能作為價(jià)值批判的標(biāo)準(zhǔn)。我要借古人的骸骨來,另行吹噓些生命進(jìn)去……”在詩(shī)歌創(chuàng)作中,他假借了中國(guó)傳統(tǒng)詩(shī)文化的自由原型與自覺原型,試圖吹進(jìn)現(xiàn)代生命的色彩;當(dāng)然,郭沫若還未曾料到,“古人”并沒有僵死,更不都是“骸骨”,它也可能對(duì)今天的新生命產(chǎn)生鞭辟入里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