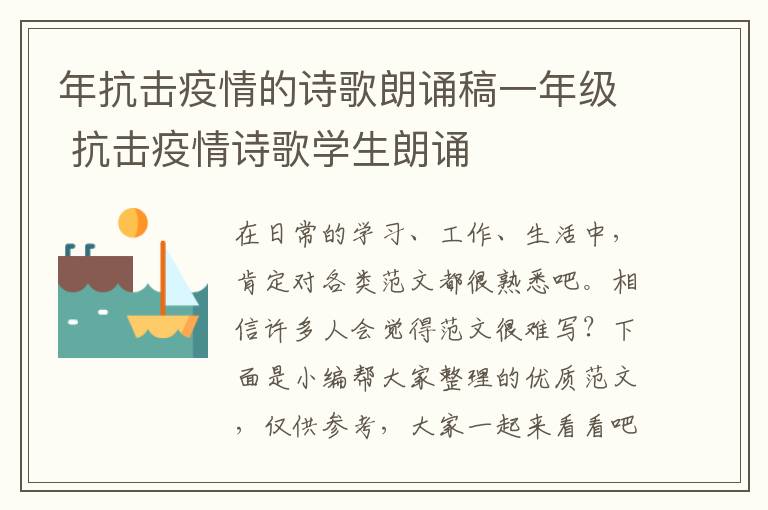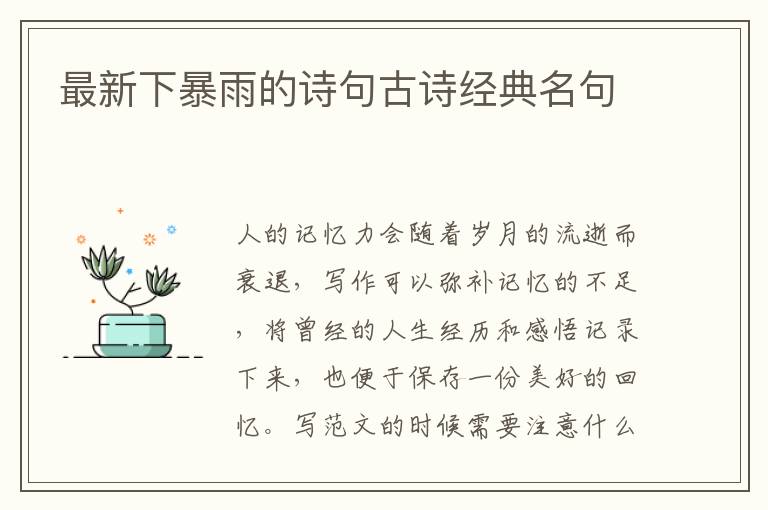西風(fēng)·氣節(jié)如花

西風(fēng)·氣節(jié)如花
西風(fēng)
她是我的文友,雖然她的文章我讀了不少,卻一直十分缺心眼兒地認(rèn)為文里那個(gè)突然得病,不能行走,成了“紙人”的倒霉女主角不是她,是別人。究其原因,也許我心里根本就不相信世界上還有這種倒霉的病。倒霉到一夜之間連絲襪也穿不上,不能刷牙,不能洗臉,不能下床,不能動(dòng)彈,按不下電話鍵,只剩眼珠還能“間或一轉(zhuǎn)”——我還以為這種叫作“行進(jìn)性肌無力”的病只不過小說里杜撰出來的呢。
還有一個(gè),也是我的文友。她的文章里面時(shí)常出現(xiàn)“輪椅”這個(gè)關(guān)鍵詞,我也仍舊十分缺心眼兒地認(rèn)為那是杜撰,這個(gè)世界哪有那么多飛來橫禍,會(huì)把一個(gè)活生生的女孩子,在17歲的時(shí)候軋成癱瘓。可是這卻是真的。
不過,這不能怪我。不是我感覺遲鈍,而是她們的文字里沒有灰色,沒有絕望,沒有玩世不恭,沒有迎風(fēng)灑淚,對月長吁,有的是對生活滿滿的珍惜、珍愛、感動(dòng)、感恩——要怪,就怪她們從不標(biāo)榜不幸。這兩個(gè)朋友,一個(gè)恢復(fù)到能打孩子,能刷牙,能洗臉,能自己坐著輪椅去衛(wèi)生間;另一個(gè),找到疼愛自己的人,坐在輪椅上結(jié)了婚。她們體會(huì)了失去一切時(shí)的艱辛,憤怒和絕望曾經(jīng)像一陣颶風(fēng),差點(diǎn)毀掉她們的生命,把她們賴以生存的信心連根拔起,于是,當(dāng)她們從泥淖中終于站起來,就變成兩個(gè)太容易快樂、太容易滿足、太容易驚喜、太容易幸福的人。
讀史,最容易讀到“氣節(jié)”兩個(gè)字。方孝孺寧肯被夷十族,也不肯起草一道詔書,是氣節(jié);文天祥百般被誘,也不肯投降元兵,是氣節(jié);屈原為什么懷石投江?亦是不肯看到自己的國家在自己的眼皮底下活活喪亡,這也是氣節(jié);就連那個(gè)不食嗟來之食的乞丐,只為要堅(jiān)持一個(gè)做“人”的尊嚴(yán),竟不惜拿命來換,這也是氣節(jié)。想來氣節(jié)這種東西如同明月,只有夜靜更深,露涼霧重,雪壓冰封,戰(zhàn)爭、動(dòng)蕩、饑荒千錘百煉,才能打造得豪氣沖天,平時(shí)的柴米油鹽、瑣碎光景里根本看不見。可是,看不見,不等于不存在。
哪怕現(xiàn)在出有車,食有魚,“活著為什么”卻成了無處不在的困擾。有的人吸毒,有的人酗酒,有的人頹廢,有的人垮掉,有的人唯我獨(dú)尊,有的人揮斥方遒,有的人行尸走肉,有的人追腥逐臭,“氣節(jié)”這兩個(gè)字,對于現(xiàn)代人來說,仍舊如色里膠青,水中鹽味,至少成為一部分人的生命底色。
這樣的人,在沒有路的時(shí)候,憑著殘疾之身,能給自己硬挖出一條路來;在厄運(yùn)來臨的時(shí)候,能把痛苦嚼碎、吃下、長出氣力,刀劍出鞘,跟命運(yùn)對峙;在完全有資格放棄和頹靡的時(shí)候,能把所有放縱的理由堵死,然后選擇堅(jiān)持,所有這些,大約都可以稱作氣節(jié)。
這樣的氣節(jié)連她們本人都沒有意識到,更沒有“作秀”的成分在,而是一種純天然的非自覺狀態(tài),既不標(biāo)榜,更不夸飾;而且它的范圍小到僅僅是對個(gè)體生命的鄭重對待,和歷史大環(huán)境中的大氣大節(jié)比起來,只能算是“苔花如米小,也學(xué)牡丹開”。但是,誰也不會(huì)想到,這兩個(gè)字支撐起來的兩個(gè)弱女子,會(huì)寫出這樣的文字:干凈、溫暖、純潔、就像一張細(xì)細(xì)密密的網(wǎng),網(wǎng)住花香,網(wǎng)住蝴蝶,網(wǎng)住幸福,網(wǎng)住愛。沐浴在它們的光輝里,就像站在北國凜冽的荒原,看到美麗的小雪花,撲閃著玉色的小翅子,飛舞得滿天滿地;又像走在涌動(dòng)的花海里,整個(gè)天地間都是令人恍惚地落了又開的繁華與美麗。
說到底,有的時(shí)候,“氣節(jié)”兩個(gè)字并不是閃著寒光的利刃,一定要刀頭飲血,對整個(gè)世界都有一種不可商量的決絕,它也可以波光瀲滟成一片溫柔的海。只要肯對自己的生命負(fù)責(zé),把凡俗的日子一天又一天認(rèn)真而美麗地過,那么,這種氣節(jié)折射出的生活態(tài)度就是被尊敬的。我們有了它,如同草有了骨,花有了心,整個(gè)時(shí)代都有了尊嚴(yán),有了香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