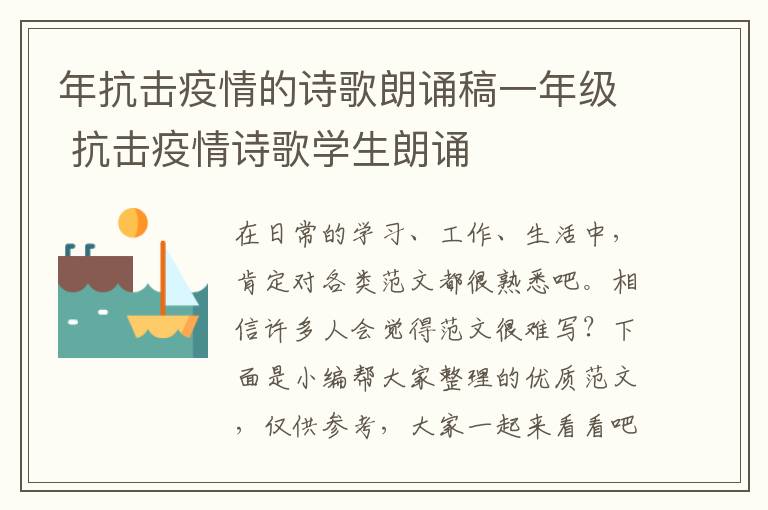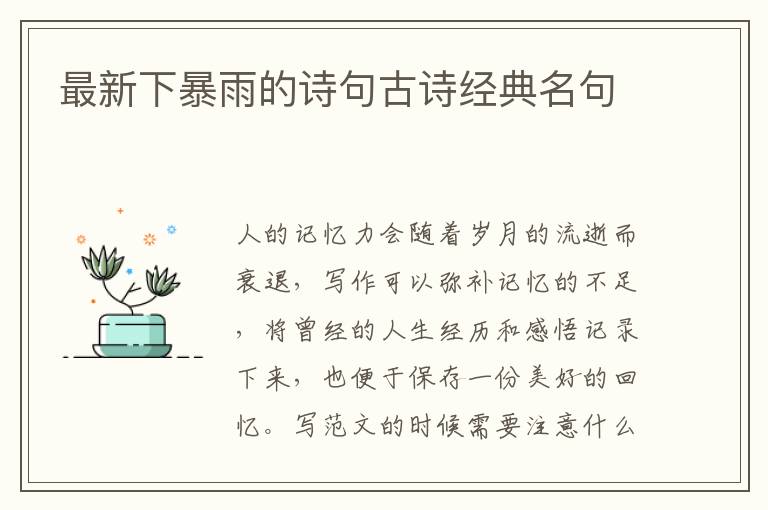孫書文《東紫的小說:“女人氣”與文學(xué)力》

東紫是一位極富“女人氣”的女作家。“女人氣”,成就了作家東紫的文學(xué)力。
“女人氣”、女作家,在相當(dāng)長(zhǎng)的時(shí)間被當(dāng)作文學(xué)力孱弱的符號(hào)。半個(gè)多世紀(jì)前,寫過《三八節(jié)有感》的丁玲就曾對(duì)“女作家”的稱謂頗有微詞:作家即作家,為何論男女。其中透露出的信息頗令人玩味。“女作家”,在中國(guó)文壇有著豐富意味,除標(biāo)識(shí)出作家的性別之外,還被賦予另外的含義。中國(guó)古代,在觀念差異、文字與文學(xué)資源稀缺的大背景中,女性只有在有意取悅于男性這一重目的之下,才有文學(xué)修習(xí)的機(jī)會(huì)與必要,文學(xué)、藝術(shù)的才能具有另外的功能性的含義。女子無才便是德,慢慢轉(zhuǎn)換為:女子有才,(往往)必然無德。中國(guó)古代文學(xué)史可以容忍大量男性易容變身創(chuàng)作出女性氣質(zhì)突顯的作品,包容了相當(dāng)數(shù)量的閨怨詩詞,但實(shí)是容不下真正的女性文學(xué)。進(jìn)入現(xiàn)當(dāng)代,這種流風(fēng)依然產(chǎn)生著影響。比如張愛玲,她身邊的胡蘭成們也成為文本解讀中不可缺少的內(nèi)容。縱然是丁玲,她與馮雪峰、胡也頻、馮達(dá)、陳明的戀情被投以極大的關(guān)注。中國(guó)當(dāng)代文壇,“女人氣”、女作家又與獨(dú)特的寫作思潮結(jié)合在一起,甚至女性寫作與身體寫作被賦予了極大的相通性。女性,成了帶有強(qiáng)烈工具性的符號(hào)。女性寫作,有些像是電影中的藝術(shù)片,追求藝術(shù)性,同時(shí)又帶有借藝術(shù)的名義以生理性因素誘人的嫌疑。宣泄著這隱私、那日記的女作家們,打著女性主義、女權(quán)主義的招牌,心中懷著為男性所不敢為的英雄之氣,創(chuàng)作著迎合時(shí)尚的作品。這一類作品,看似有著強(qiáng)大的文學(xué)力,但從文學(xué)的常識(shí)、甚至從生活的常識(shí)而言,其實(shí)是落了下道。領(lǐng)風(fēng)騷幾年后,這類文字雖還余音裊裊,但已成不了氣候。“美女作家”這一文學(xué)符號(hào),在大眾合力制造美女的時(shí)代,更多帶有調(diào)侃的味道。
同時(shí),誰也抹殺不了性別存在的事實(shí)。自然造物,便有男女。社會(huì)的磨洗,更是強(qiáng)化了這種觀念。波伏瓦提出“第二性”的觀念,指出女性不是先天形成,更多是后天造就。從另一個(gè)角度看,“女人氣”恰恰是在特定生理基礎(chǔ)上流溢出的性別特征。這種特征會(huì)影響作家的文體創(chuàng)造。同是寫雨后場(chǎng)景,李清照(“惜春春去,幾點(diǎn)催花雨”)便與蘇東坡(“回首向來蕭瑟處,歸去,也無風(fēng)雨也無晴”)不同。同樣寫海,冰心的海(“我對(duì)它的愛是歸心低首的”)與峻青的海(“一排排山嶺似的巨浪從那灰黑色的遙遠(yuǎn)的天際,以排山倒海之勢(shì)呼嘯著咆哮著向著岸邊滾動(dòng)過來”)便有不同。英國(guó)作家莫里斯,經(jīng)歷了變性手術(shù),性別的轉(zhuǎn)換影響了其對(duì)世界觀察、體認(rèn)的角度,創(chuàng)作的風(fēng)格也為之大變。誰也不能抹殺女作家獨(dú)特的性別特征,正如同不能抹殺作家的年代軌跡,不能抹殺作家的地域特征。作家是復(fù)雜的組合體。年代、地域,這些所謂的外部因素在許多時(shí)候會(huì)對(duì)作家產(chǎn)生潛移默化、又會(huì)是深入骨髓的塑造力。例如,中國(guó)50后作家對(duì)理想的執(zhí)著,80后作家骨子里的叛逆;俄國(guó)作家傾向于探挖心靈的深度,美國(guó)作家則傾向于對(duì)外在世界奧妙的探險(xiǎn);等等。性別作為更為內(nèi)在性的因素,也可與時(shí)代、地域等因素一樣,成為一個(gè)作家之文學(xué)力的重要來源。
“女人氣”,成就了作家東紫的文學(xué)力。女作家東紫,善于、喜愛書寫女性。她的作品營(yíng)建了一個(gè)女性形象的畫廊:碧玉(《一棵韭菜的戰(zhàn)爭(zhēng)》)、姚遙(《左左右右》)、被大鳥綁架的“我”(《我被大鳥綁架》)、印小青(《顯微鏡》)、梅云(《春茶》)、紫月(《被復(fù)習(xí)的愛情》)、小王子丹(《穿堂風(fēng)》)、麥粒(《同床共枕》)、王小丫(《好日子就要來了》)……這是一個(gè)帶有強(qiáng)烈“女人氣”的女性形象系列:潔凈、輕盈、不為世俗污垢所染,不通凡間世故甚而有些不食人間煙火。“碧玉在田壟上輕邁著細(xì)碎的步子,春天早晨的微風(fēng),溫潤(rùn)清涼,拂動(dòng)著她淡綠色的衣裙。碧玉覺得近日來堵在心里的那股氣體慢慢地隨了風(fēng)向后飄去,自己的身體變得輕盈通透,如同從泉水里洗過的紗巾,被一雙纖細(xì)白皙的手拽起,抖落了細(xì)碎的水珠,在風(fēng)里飄動(dòng)。她的腳步歡快起來,露珠在她繡著粉色荷花的鞋面上滴落、浸潤(rùn),她的腳趾也體會(huì)到了一種清涼。那種不同于雨水有別于泉水的清涼是調(diào)皮的、嬉戲的,輕輕地在你不注意的時(shí)候?yàn)⒙涞摹!薄兑豢镁虏说膽?zhàn)爭(zhēng)》發(fā)表于2007年,其中的碧玉,凝結(jié)著作家東紫關(guān)于女性的形象的理想。后來的印小青、梅云、小王子丹或隱或顯都有一個(gè)“碧玉”的底子。碧玉是身由不己地“誤食”了一棵韭菜,釀成悲劇。這棵韭菜,在梅云那里則變成了一段未加控制、甚至有意加醇的感情。造化弄人,在造化面前,女性命運(yùn)顯現(xiàn)出鮮明的吊詭特征。寫順手了女性,到2010年的《白貓》,東紫也試圖做一改變:敘述者“我”化身為一個(gè)為情所困、有待啟蒙的五十歲男性。但這一形象,在他那位拿得起放得下、充滿權(quán)力感、習(xí)慣俯視別人的醫(yī)學(xué)博士前妻的襯托之下,若不是刻意點(diǎn)明性別,整體看來卻反而具有鮮亮的“女人氣”:處處不設(shè)防,因而總受傷;隨遇而安,只要世界讓我過得去,我決不與世界為難;用生病來考驗(yàn)自己的戀人,找一個(gè)愛我的人,而不是我愛的人。這一次“失敗”的變身實(shí)驗(yàn)似乎也說明了,寫女性,是東紫的“宿命”。
在這一系列形象身上,東紫頗為“任性”地書寫著生理體驗(yàn)以及由這些生理體驗(yàn)引發(fā)的一系列“女性問題”,洞開心扉,不加隱藏。比如,她寫男女之間的沖突:一個(gè)男人的呼嚕會(huì)成為戕害一個(gè)女人青春的殺手;比如,初為人母,充滿喜悅與溫柔,但也不乏壓抑與痛苦。這些含蘊(yùn)隱喻的生理體驗(yàn),在東紫的筆下,無不帶有強(qiáng)烈的“女人氣”:重直感,重細(xì)節(jié),她用生理感覺牽引出對(duì)生活細(xì)切的體驗(yàn)。東紫善于寫氣味。《天涯近》中,大寶家的臥室、走廊里洋溢的是酸腐的味道,繼母、父親、玉兒都帶著酸腐的味道,驕陽下的整個(gè)世界都帶有了這樣的味道。玉兒叫他“少爺”時(shí),他聞到了鴉片的香味。他的世界與豐雨順世界的區(qū)別也在于氣味。東紫“放肆”地運(yùn)用自己女性的敏感,描寫生理現(xiàn)象引發(fā)讀者的生理反應(yīng),開拓進(jìn)入審美體驗(yàn)的窗口。她筆下的“痰”便無與倫比、卓絕古今:“或濃或淡,或黃或白,或半固體或液體,或陳舊或新鮮,或光滑或夾雜著泡泡,或成噴射狀或蜷曲一團(tuán)”,帶著聲響的“嗬,呸,啊,噗”,往下看,“前面的人抬起的鞋掌下,有一縷扯不斷的黏稠”,往上看“一個(gè)喘著白色粗氣的嘴巴張開,一口飛奔而出的唾沫劃過印小青眼前淡淡的霧落下去”(《顯微鏡》)。她恨透了“痰”,于是才有這樣的激情與能量充分調(diào)動(dòng)人的生理體驗(yàn)。東紫寫生活,寫得帶有“女人氣”的任性,不講道理,聽?wèi){情感的驅(qū)遣。但也正因如此,她能把生活本身描繪得細(xì)膩而有質(zhì)感。在她的創(chuàng)作之中,女醫(yī)生的形象或隱或顯,印小青、姚遙……女性本就有著比男性更為敏感的生理感受,醫(yī)生的這一層因素又把這種能力銳化、豐富。
東紫重視生活中的小溫情,對(duì)生活懷著樸素的情感。她把存在主義、現(xiàn)代主義、女權(quán)主義、后現(xiàn)代主義……擱置在她那顆重直覺的心靈之外。《天涯近》中的豐雨順,父親死了,妻子跑了,兒子傻了,似乎什么也沒有了,但依然在追求快樂,單單是溫暖的陽光便能給他無限的希望。《在樓群中歌唱》中做小區(qū)環(huán)衛(wèi)工的李守志,一遍一遍重復(fù)著《我在馬路邊撿到一分錢》的童謠,安享著簡(jiǎn)單的幸福。唱著歌干活,這是李守志女兒歡喜的愿望,也是作家的愿望。白貓的“愛情”故事打動(dòng)、改變了“我”的愛情態(tài)度,重拾對(duì)美好愛情的追求(《白貓》)。《好日子就要來了》是東紫一篇長(zhǎng)篇小說,題目所示即是她內(nèi)心的呼喚。她是對(duì)生活存有溫情的作家,多有批判但很少能將殘酷進(jìn)行到底,總樂意增加些溫色調(diào),或者有一個(gè)透進(jìn)陽光的結(jié)尾。苦難之中堅(jiān)守快樂,歷盡艱難不舍希望,這是東紫小說中最為動(dòng)人的因素。她寫了許多極端事件、極端體驗(yàn),但同時(shí)又往往把極端事件、極端體驗(yàn)“鈍化”,很少寫直接的、視覺化的生理沖突。渴望溫暖、互相溫暖,她希望她的小說世界洋溢著溫情。
從東紫的寫作看,這種溫情并無深沉似海、大苦大難的生存背景,賴以支撐的僅僅一種平常、平凡卻又蔓延彌漫的寬容。這體現(xiàn)為作家執(zhí)著的“母儀天下”的女性情懷。“我”對(duì)白貓、自己的兒子,充滿了關(guān)愛:“貓?jiān)谖业淖鴫|上仰躺著睡著了,那樣子非常像嬰兒。我一下子想起兒子不滿一歲的時(shí)候,那時(shí)候他胖得和白貓差不多,睡覺的時(shí)候把兩只小胖手攥得緊緊的放在耳朵邊上。”白貓失蹤,“我”洗了它的照片,拿著四處尋問,跑遍了周圍的各個(gè)住宅小區(qū)、建筑工地、動(dòng)物收留站、餐館(《白貓》)。牟琴想樂樂,為樂樂擔(dān)心,冒著得罪全家人的危險(xiǎn)到陌生的村子里去探看,展示出一個(gè)充滿了母愛的女性才有的戰(zhàn)斗的姿態(tài)。無辜的樂樂,忍受這個(gè)世界所有人的罪過,牟琴的義無反顧折射出東紫的母性情懷(《樂樂》)。一名殘疾孩子,讓印小青的母性蓬勃爆發(fā)(《顯微鏡》)。《互相溫暖》是東紫用力頗多的一篇作品,在思想層面的努力下探使其顯得獨(dú)樹一幟。老三們活得正常而風(fēng)光,他們追逐著金錢與門面,把這個(gè)世界變得功利而狹隘,讓這個(gè)世界在表面的光鮮之下生機(jī)喪失殆盡。他們?nèi)莶坏没剂藨傥锺钡睦纤牡拇嬖凇=o這個(gè)世界以生機(jī)的是兩位母親——老四的母親與“外村女人”。她們寬容、放任為自我而活、始終是孩子的老四。老四所依戀的乳罩,是母性的象征,有著深沉的力量。
批評(píng)家提到“女人氣”時(shí),往往還經(jīng)常加上一“小”字,成為“小女人氣”:封閉、偏執(zhí)、自戀、做作,與開放、大度、大愛、從容相對(duì)。“女人氣”實(shí)在不必然便成為“小女人氣”。與偉大相對(duì),有一種細(xì)切,可以精致而勇猛,生鮮而具體。東紫的成功在于,她把“女人氣”化成一種隱忍的寫作力道,成就了自己的文學(xué)力。在她的小說中,有一個(gè)沉默的層面存在;許多時(shí)候,小說的力量恰恰在于欲言還休之處。她是一位有意于創(chuàng)造自己文體的作家,對(duì)于怎樣打造自己創(chuàng)作的利器,她有著思考并進(jìn)行實(shí)踐的探索。2007年,是東紫的實(shí)驗(yàn)?zāi)辏?008年,則是她創(chuàng)作上的“迷亂期”。這兩年間,她發(fā)表的作品有:《左左右右》、《邂逅》、《我被大鳥綁架》、《顯微鏡》、《夢(mèng)里桃花源》、《珍珠樹上的安全套》。《左左右右》沿襲了此前《珍珠樹上》、《天涯近》的路向,并向前做了推進(jìn),更加圓熟自如;但她試著突圍,進(jìn)行了一系列的實(shí)驗(yàn)。《邂逅》是要走抓人內(nèi)心隱秘閃念路子,有心理小說的氣象;《一棵韭菜的戰(zhàn)爭(zhēng)》,是要走離奇故事的路子,把人性的糾結(jié)放于方寸之間;《我被大鳥綁架》,帶有強(qiáng)烈的實(shí)驗(yàn)小說的味道。2007年多向度的實(shí)驗(yàn),衍生的是2008年的“迷亂”。《夢(mèng)里桃花源》欲走討巧之路。小時(shí)的饑餓體驗(yàn),或許加之《饑餓藝術(shù)家》之類作品的閱讀體驗(yàn),促成了這一文本。同時(shí),東紫又有意要擺脫單純的生理體驗(yàn)的書寫,加入了夢(mèng)幻與真實(shí)不可分的重要理念。作品雜糅但不豐實(shí),生理的惡心與觀念指歸的虛空結(jié)合一起,沒有促成預(yù)期的閱讀體驗(yàn)。《珍珠樹上的安全套》為2004年《珍珠樹上》的縮寫版,可能是為了雜志欄目之需,帶有作家作品展演性質(zhì),同時(shí)在題目中突顯了本為撩人胃口實(shí)為倒人胃口的字眼。可幸的是,在《顯微鏡》中,東紫又走回到了堅(jiān)實(shí)的路上。此后的《在樓群中歌唱》、《樂樂》等等,加固了這條堅(jiān)實(shí)的道路。
一路下來,東紫成功的小說,都是在著意于給人以溫暖。《互相溫暖》富有深意:老四與“外村女人”,都是溫暖的施予者,也都是溫暖的接受者。放眼看來,“互相溫暖”也是東紫小說核心理念所在:樂樂收獲了牟琴一家人的溫暖,牟琴一家人在溫暖樂樂的同時(shí),也溫暖自己一家人;“我”關(guān)愛白貓,白貓的愛情也使“我”的心重獲溫暖。文學(xué)何為?可以批判,可以警示,更為重要者:安頓心靈。于創(chuàng)作者而言,要在寫作中安頓自己的心靈。就閱讀者來說,是在文字中尋找心靈的港灣。
作家或許本就是要有些“女人氣”的。古希臘神話中,奧林匹亞山上主管文藝的是繆斯女神。印度傳統(tǒng)中,文藝之神是身坐蓮花寶座之上的大梵天的妻子。對(duì)生活的敏感,對(duì)溫情的執(zhí)著,對(duì)母性的堅(jiān)守,這是女作家文學(xué)力的重要源泉。冰心、張愛玲、丁玲、王安憶、畢淑敏、遲子建……這些筆觸細(xì)膩而溫婉、思緒靈動(dòng)而敏捷、柔韌聰慧、純良寬容的女作家搭建了一道靚麗的風(fēng)景。聽從心靈的命令,生活在高處,“紫氣東來三萬里”,東紫這位有著強(qiáng)烈“女人氣”的女作家有理由帶給文壇更多的驚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