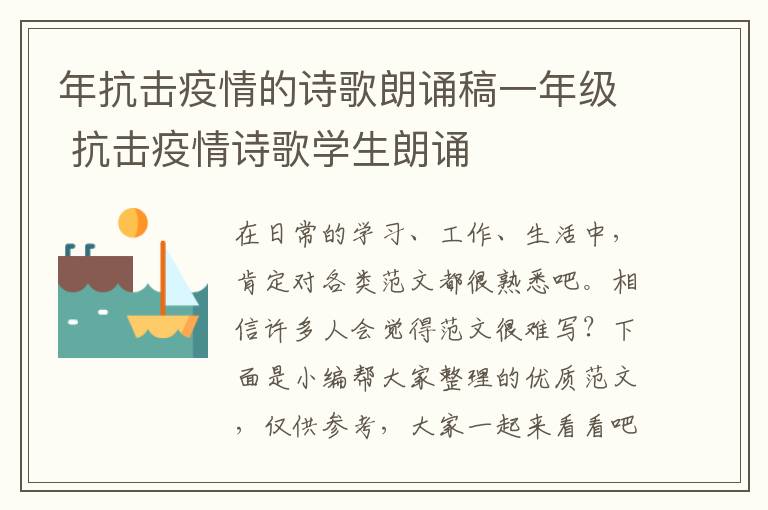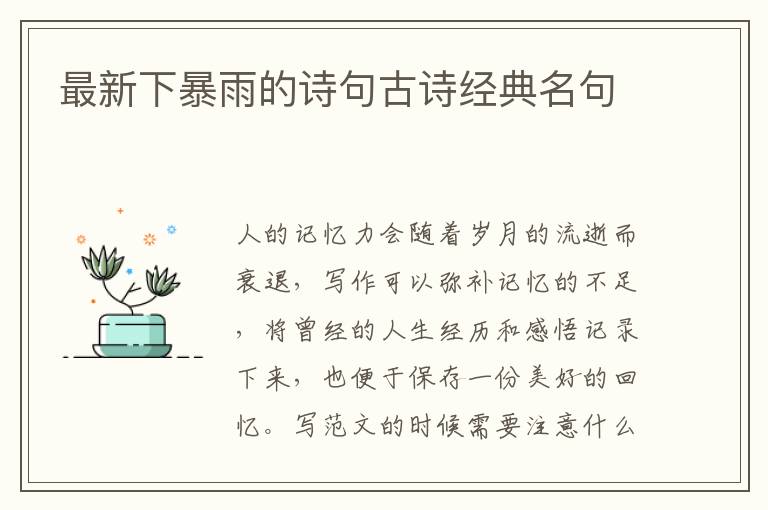湯顯祖戲曲作品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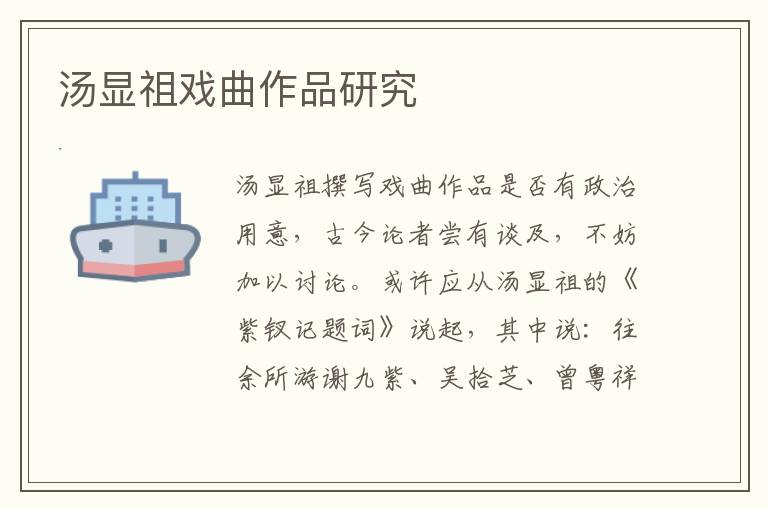
湯顯祖撰寫戲曲作品是否有政治用意,古今論者嘗有談及,不妨加以討論。
或許應(yīng)從湯顯祖的《紫釵記題詞》說起,其中說:
往余所游謝九紫、吳拾芝、曾粵祥諸君,度新詞與戲,未成,而是非蜂起,訛言四方,諸君子有危心,略取所草具詞梓之,明無所與時(shí)也。記初名《紫簫》,實(shí)未成。
《紫簫記》作于萬歷七年(公元1579年)左右,《紫釵記》作于萬歷十六年(公元1588年)前后。湯顯祖所說“度新詞與戲”,到了萬歷四十年(公元1612年)前后刊行的呂天成《曲品》中,有了具體說法,其《紫簫記》條有云:“向傳先生作酒、色、財(cái)、氣四記(一作犯),有所諷刺,是非頓起,作此以掩之,僅半本而罷。”而在沈德符的《萬歷野獲編》中,《紫簫記》本身成了確實(shí)的“填詞有他意”的事例:“又聞湯義仍之《紫簫》,亦指當(dāng)時(shí)秉國(guó)首揆,才成其半,即為人所議,因改為《紫釵》。”按照這個(gè)說法,湯顯祖撰寫《紫簫記》,具有譏彈“首揆”即首輔,也即首相的用意。
晚近學(xué)人董康匯輯清人《樂府考略》,改名《曲海總目提要》,并私撰“江都黃文旸原本”字樣,其中《紫釵記》條引錄了上述《野獲編》的說法,但無考訂并引申。而在《邯鄲記》條中卻明說此劇有指責(zé)首輔張居正和申時(shí)行的寓意:
萬歷五年為丁丑科,首輔張居正欲其子及第,因網(wǎng)羅海內(nèi)名士,聞顯祖及沈懋學(xué)名,命諸子延致之。顯祖獨(dú)勿往,懋學(xué)遂與居正子嗣修偕及第。是科嗣修卷,大學(xué)士張四維次名二甲第一,既進(jìn)御,神宗啟姓名,則拔嗣修一甲第二。而謂居正曰:無以報(bào)先生功,貴先生子以少報(bào)耳。其得鼎甲也,乃出帝意云。顯祖既下第,至(萬歷)十一年始成進(jìn)士,授南京博士。時(shí)申時(shí)行為首輔,顯祖負(fù)大才,以不得鼎甲,意常怏怏,故借盧生事以抒其不平。指其時(shí)之得狀元者,藉黃金,通權(quán)貴,故云:“開元天子重賢才,開元通寶是錢財(cái)。若道文章空使得,狀元曾值幾文來。”其指閱卷之宰相則云:“眼內(nèi)無珠作總裁。”譏之如此。
《樂府考略》中還說:“按嘉靖壬戌科鼎甲三人:申時(shí)行、王錫爵、余有丁皆入閣,而曲本盧生、蕭嵩、裴光庭皆以同年鼎甲入相,作者亦有寓意也。”
《樂府考略》的作者(當(dāng)不止一人)姓名無考,但可推知是清中葉人。他實(shí)際上并無新材料可坐實(shí)明人沈德符的“填詞有他意”說,只是籠統(tǒng)地把《邯鄲記》第六出《贈(zèng)試》所寫盧生妻子打點(diǎn)金錢為丈夫“前途賄賂”情節(jié)和該出下場(chǎng)詩(shī)說成是影射明代科場(chǎng)腐敗。《邯鄲記》第七出《奪元》寫黃榜招賢,主試官原擬取媚權(quán)貴,錄取武三思之婿裴光庭為第一名,殊不料“御覽”裁定盧生第一、蕭嵩第二、裴光庭第三,主試官自嘆“他(指盧生)的書中有路能分拍,道俺眼內(nèi)無珠做總裁。”《樂府考略》撰者予以引用,也認(rèn)為是對(duì)明萬歷帝擢拔張居正之子張嗣修科名的譏刺筆墨。按《邯鄲記》系據(jù)唐人《枕中記》改編,原著者稱是記唐開元間事,實(shí)多虛構(gòu),湯顯祖改編更有異想之筆,劇中也確有對(duì)上層官場(chǎng)乃至皇帝的不敬言語和譏諷筆墨,若說其中概括有作者當(dāng)時(shí)的若干官場(chǎng)經(jīng)歷和見聞,也或合創(chuàng)作理路,但是否可確認(rèn)是湯顯祖對(duì)萬歷帝、張居正和申時(shí)行的批評(píng)和抨擊,難以考實(shí)。或許只是后世論者據(jù)《明史》有關(guān)記載而對(duì)湯劇所作的想當(dāng)然猜測(cè)而已!至于把湯顯祖原序說到的《枕中記》中原有的“通漕于陜,拓地于番”內(nèi)容說成是影射“申時(shí)行輩”,把劇中“摹寫沉著聲戀于聲勢(shì)名利之場(chǎng)”種種情節(jié)說成是“為張居正寫照”,更嫌穿鑿。近代曲家也有附和此說而認(rèn)為湯顯祖是“借此泄憤”的,還有的曲家認(rèn)為湯顯祖在《邯鄲記》中多用諷刺是為了“喚醒”張居正。按當(dāng)下研究家大抵認(rèn)為《邯鄲記》作于萬歷二十九年(公元1601年),其時(shí)距張居正去世的萬歷十年(公元1582年)已近二十年,此時(shí)此際的湯顯祖,還念念不忘,睚眥必報(bào),竟要借寫戲機(jī)會(huì),予以諷刺、撻伐,違背常情,離開禮數(shù),與古人之道不合。還有的曲家認(rèn)為劇中盧生系湯顯祖“自謂”,更屬奇談怪論。
《樂府考略》的作者認(rèn)為《牡丹亭》中也有“托時(shí)事以刺貴要”的內(nèi)容,并大作索隱,且文字冗長(zhǎng),今約為三點(diǎn):
1.劇中杜寶影射鄭洛。鄭洛于明代隆慶、萬歷時(shí)期曾任侍郎,為了得到“經(jīng)略”之職,不惜以女兒作交換籌碼,《樂府考略》中說:“廣西人蔣遵箴,為文選郎中,聞鄭(洛)女甚美,使人謂曰:以女嫁我,經(jīng)略可必得也。鄭以女嫁之,果得經(jīng)略。”《樂府考略》作者認(rèn)為,鄭洛是保定人,“近畿”,即靠近明時(shí)京都北京。劇中人杜寶是杜陵人,“而杜陵最近長(zhǎng)安”,即靠近唐時(shí)京城,“故以為比也”。《樂府考略》作者又認(rèn)為,劇中柳夢(mèng)梅是影射索娶鄭女的蔣遵箴,因?yàn)槭Y是廣西人,而柳夢(mèng)梅是唐朝柳州司馬柳宗元之后,留家?guī)X南,“柳州在廣西,故云柳,又曰嶺南也”。
2.劇中寫杜寶命陳最良招降早已降金的李全夫婦是影射明代官府招降韃靼俺答部。《樂府考略》中說:“隆慶時(shí),總督王崇古招俺答來降,封為順義王,其妻三娘子封忠順夫人。由是邊督之缺,為時(shí)所慕。自方逢時(shí)、吳兌以后,其權(quán)愈重,稱曰經(jīng)略。”《樂府考略》作者認(rèn)為劇中李全之妻是影射三娘子,并說第四十七出《圍釋》中陳最良對(duì)李全妻子說:“但是娘娘要金子,都來宋朝取用。”這就是影射明朝大臣吳兌和鄭洛等人,因?yàn)?ldquo;時(shí)吳兌等以金帛結(jié)三娘子,兌遺以百鳳裙等服飾甚眾,(鄭)洛亦可知,故云然也。”《樂府考略》作者還說,劇中第五十五出《圓駕》,柳夢(mèng)梅譏刺杜寶,“你則哄的個(gè)楊媽媽退兵”,并說杜寶并未討平李全,“只平的個(gè)‘(李)半’”“(李)半”指李全夫妻的一半。而楊媽媽即指李全妻子楊氏。《樂府考略》作者說:“(鄭)洛等前后為經(jīng)略,皆結(jié)納三娘子,三娘子能鉗制俺答,又能約束蒙古,故以‘平得李半’譏之也。”
3.柳夢(mèng)梅姓名中有兩個(gè)“木”字,也是譏諷手法。《樂府考略》中說:“柳夢(mèng)梅姓名中有兩木字,時(shí)丁丑科狀元沈懋學(xué)、庚辰科狀元張懋修、癸未科榜眼李廷機(jī),皆有兩木字。丁丑、庚辰,顯祖下第,癸未又不得翰林,故暗藏此以譏之也。”
除了上述三點(diǎn)外,還把劇中的“識(shí)寶使臣”苗舜賓視為影射戊子年北闈主試官黃洪憲,因“‘黃’字抽出數(shù)筆是為‘苗’字”。而柳夢(mèng)梅又是影射被黃洪憲取中的李鴻,等等,不再贅引。
按《牡丹亭》并非歷史劇,作者虛構(gòu)設(shè)定的故事背景是宋代(南宋),劇中即使岀現(xiàn)實(shí)有歷史人物,其行動(dòng)、語言卻盡多虛構(gòu)。其間種種描寫,折射作者的生活經(jīng)歷和現(xiàn)實(shí)見聞,正是文藝創(chuàng)作規(guī)律的表現(xiàn),但如果認(rèn)為這種折射可以一一確指現(xiàn)實(shí)人物、事件,那就謬以千里了。中國(guó)古時(shí)俳優(yōu)表演,所謂優(yōu)孟衣冠,參軍滑稽,確有譏謔時(shí)事,托諷匡正的內(nèi)容,也形成一種傳統(tǒng),宋元以來,戲曲中也不時(shí)可見此類內(nèi)容穿插劇中,以調(diào)劑戲劇氛圍。但像《樂府考略》作者所作所言,已超越這類范圍,而屬人物和劇情索隱。其牽強(qiáng)附會(huì),主觀穿鑿,幾達(dá)極致。真可說是可憐無補(bǔ)費(fèi)工夫。至于把劇中人物杜寶、柳夢(mèng)梅說成是影射多種人物事件的角色,更屬匪夷所思。有的近代曲家也予以批評(píng),謂之“癡人說夢(mèng)”。
《樂府考略》作者說《牡丹亭》“其言外或別有寄寓”,從而所作的種種索隱猜測(cè)的根據(jù)是湯顯祖對(duì)自己仕途坎坷的不滿:“(湯顯祖)官禮部主事,上疏劾首輔申時(shí)行,謫徐聞典史,稍遷遂昌知縣,(萬歷)二十七年大計(jì)奪官,顯祖頗多牢騷,所作傳奇往往托時(shí)事以刺貴要。”且不說這種猜測(cè)不符合湯顯祖在《牡丹亭題詞》中的自我申述,如果這種不滿真的成為《牡丹亭》主要寫作動(dòng)機(jī),那湯顯祖也就不會(huì)成為一位杰出作家了。
為了附會(huì)政治,對(duì)文藝作品作支離破碎的穿鑿解讀,或許可上溯到漢儒注釋《詩(shī)經(jīng)》,代代相傳,不僅影響到唐詩(shī),也影響到對(duì)宋元以來的詞曲解讀,南宋《復(fù)雅歌詞》的編選者解讀蘇軾詞作《卜算子》就屬附會(huì)曲解的著名例子。蘇詞全文是:
缺月掛疏桐,漏斷人初靜。誰見幽人獨(dú)往來,縹緲孤鴻影。
驚起卻回頭,有恨無人省。揀盡寒枝不肯棲,寂寞沙洲冷。
這是蘇軾在黃州時(shí)的作品,詞詠夜景,寫及孤鴻,或有寄托,但被《復(fù)雅歌詞》的選者解釋得支離破碎:“‘缺月’,刺明微也。‘漏斷’,暗時(shí)也。‘幽人’,不得志也。‘獨(dú)往來’,無助也。‘驚鴻’,賢人不安也。‘回頭’,愛君不忘也。‘無人省’,君不察也。‘揀盡寒枝不肯棲’,不偷安于高位也。‘寂寞沙洲冷’,非所安也。與《考盤》詩(shī)極相似。”清代著名詞人張惠言卻表贊同,他在《詞選》中予以全文引錄。
王國(guó)維《人間詞話》批評(píng)這種牽強(qiáng)之論說:“子瞻《卜算子》,皆興到之作,有何命意?皆被皋文深文羅織。”“皋文”即指張惠言。王國(guó)維同時(shí)節(jié)引清人王士禎批評(píng)《復(fù)雅歌詞》選者的話,王士禎說:“村夫子強(qiáng)作解事,令人欲嘔……仆嘗戲謂:坡公命宮磨蝎。湖州詩(shī)案,生前為王珪、舒亶輩所苦,身后又硬受此差排耶!”據(jù)《宋史·蘇軾傳》,御史李定、舒亶和何正臣等人以蘇詩(shī)“訕謗”為由,鍛煉成獄,欲置蘇軾于死地。王士禎把“差排”和“訕謗”二者相提并論,雖稱“戲謂”,卻可見出他十分厭惡牽強(qiáng)附會(huì)之情。
《復(fù)雅歌詞》選者“差排”蘇軾,曲解《卜算子》,其出發(fā)點(diǎn)是說君臣大義,由于君王不察,使得賢人失志,也就是所謂“刺”,他把蘇軾比作賢人,所說“愛君不忘”,則屬“怨而不怒”,所以謂之“雅詞”。“美刺”本也是古人研究《詩(shī)經(jīng)》時(shí)得岀的一種傳統(tǒng)的文雅說法,但像《樂府考略》作者解讀《牡丹亭》那樣,竟說湯顯祖不僅譏刺封疆大吏,就連同時(shí)科考之人也予譏彈,原因只是他們得第,而湯顯祖自己落榜。這類說法,不知置湯顯祖于何地!于此卻倒說明,此類索隱已趨入末流了。類似這樣的索隱臆說,因有古老傳統(tǒng),難以絕跡,清末民初之際,暖紅室刊本的跋文中就有驚聽之語,可能是鑒于《牡丹亭》的《冥判》岀多有諷世描寫,跋文作者認(rèn)為這是“見道之文”,并作岀胡判官是劇作者“自謂”,是湯顯祖“現(xiàn)身說法”的臆斷。不顧全劇的主題內(nèi)容,追求所謂“傳外寓意”,肢解作品,舍本逐末,執(zhí)一而論,其實(shí)際結(jié)果也就成為虛詞詭說了。